
生生的秩序——汉字中的植物与时间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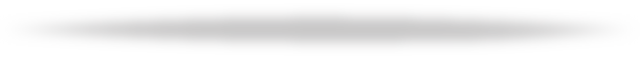
文/孟琢 史瑞雪
时间观念的形成,伴随着人类精神自觉的晨曦。时间,是文明与历史的内在框架,奠定了一个民族精神方式的基本特质。中国古代的时间观念来自何处?它有着怎样的文化特点?时间,与天地人物的规律与秩序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?关于先民的时间奥秘,我们可以在同样古老的汉字中探究一二。

时间无形,汉字有象,古人为时间造字,往往取象于时间的标志物。日月运行,循环不息,这是最为常见的时间标志。“日、时、昼、旦、晨、早、朝、晚、晌、暮、昏”,一天中的光阴变化,体现在太阳的起落升降中;“夕、宵、夜、閒、朔、望”,清幽的夜色,月份中的光阴流转,寄寓在明月的阴晴圆缺里。一日一月标志的时间相对短暂,至于更为长久的时间节奏,则与汉字中的植物意象密不可分。在历史悠久的农耕社会中,植物的岁岁枯荣、农作物的生长成熟、播种的辛苦、丰收的喜悦,都积淀为古人重要的时间坐标。

关于植物与时间,还是要从“时”字说起。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时,四时也。从日寺声。旹,古文时从之、日。”在甲金文中,“时”写作

、

,从日从之,这是《说文》古文的形体来源。“时”造字取象于“日”,但若探其词源,与植物的耕种亦密不可分。先秦汉语中,“時”与蒔、植、殖等同源,皆与植物的生长种植有关。许慎把“蒔”解释为“更别种”,也就是重新播种、移栽秧苗的意思。段玉裁解释说:“《方言》曰:‘蒔,立也。蒔,更也。’《尧典》:‘播时百谷。’郑读时为蒔,今江苏人移秧插田中曰蒔秧。”在文献中,“蒔”和“时”音近义通,往往假借;它既训为“立”,也训为“更”——栽下新的萌芽,寄托新的期望,正是年岁更迭、时光开启的象征。《考工记》中说:“天有时以生,有时以杀;草木有时以生,有时以死,石有时以泐;水有时以凝,有时以泽:此天时也。”《说苑·建本》说:“鱼乘于水,鸟乘于风,草木乘于时。”在草木的生长循环中,蕴含着中国人的时间秩序。

“时”为四时,最初指春夏秋冬的整体运作,而不是泛化的时间单位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说:“凡言时,若《尧典》之四时,《左氏传》之三时,皆谓春夏秋冬也。”段玉裁说:“(时)本春秋冬夏之称,引伸之,为凡岁、月、日、刻之用。”准确说解了“时”的范围。一年四季,以“春秋”为要,它们既是关键的农时节点,也是《春秋》纪年的历史标志。在这两个字中,也体现出鲜明的植物意象:
先看“春”字,它在甲文中作

,在小篆中作

。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春,推也。从艸从日,艸春时生也,屯声。”艸为植物,日为阳光——春日迟迟,阳光普照,青草丛生,覆盖大地。至于“屯”字,也是小草破土而生之形。小篆作

,其上为“一”,代表大地;下部是“屮”,为草芽之象形——在大地冰封之下,草芽努力生长,虽然被坚硬的冻土压得蜷缩起来,但终究崭露头角、露出新芽。在《周易》中,“屯”为卦名,“屯,刚柔始交而难生”,亦寄寓了在压力中奋力突破的内涵。在“春”字里,展现出万物苏生的蓬勃气象——柔弱的小草积蓄力量,在温暖的春光中破土而出,焕发出强旺的生命力。这一意象,也是《老子》“柔弱胜刚强”的鲜活写照。再看“秋”字,在甲骨文中,秋写作

、

,像只活灵活现的蟋蟀,有人说它借为“秋”字,有人说秋虫是秋天的象征。到了战国文字之后,“秋”多从“禾”,睡虎地秦简写作

,《说文》小篆作

,遂有了今天的“秋”字。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秋,禾谷孰也。”段玉裁解释道:“其时万物皆老,而莫贵于禾谷,故从禾。言禾复言谷者,晐百谷也。”秋天是收获的时节,百谷成熟,禾穗低垂,以此作为秋季的象征;谷物一年一熟,“秋”也用作“年”的代称——所谓“千秋万岁”,正是“千年”之义。

“日月忽其不淹兮,春与秋其代序”,春秋和日月一样,都是时间的重要节点。所区别者,前者纪日、纪月,以天象为标志,是时间的“小循环”;后者纪年,以草木为标志,是时间的“大循环”。“春”是草木的生生不息,“秋”是谷物的丰硕成熟。由“春”到“秋”,植物的萌芽、繁盛、收获、潜藏,为时间赋予了鲜明的节奏;由“生”到“成”,千百年来的农耕生活,更积淀为中国文化内在的积极态度——虽然生灭相依、成毁相随,但中国人观察世界的目光,向来注重生生之道,而不似佛法那样偏重生灭无常。某种意义上,这与“春生秋成”的搭配模式不无关系——“生”的归宿不是“灭”,不是悲观的消逝与虚无,而是“成”,是令人欢欣鼓舞的、属于现世的收获。
“生”与“成”,这两种时间的气质与节奏,也体现在古代表示“年岁”的汉字中。关于“生”,古人用“茲”来表示年岁,就取自滋生之意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:“今茲未能,请轻之,以待来年。”“今茲”和“来年”相对为文。《吕氏春秋·任地》:“今茲美禾,来茲美麦。”高诱注:“茲,年也。”“茲”字从艸,其本义为“草木多益”,与滋生的“滋”同源。章太炎先生曾在日本为鲁迅、钱玄同、朱希祖等人讲授《说文解字》,这份珍贵的课堂笔记至今存留,钱玄同记录道:“草木多益也,引申为凡多益之称。今兹者,今年也,自去年言之又多一年也,故曰今兹。”在太炎先生看来,古人用“茲”来表示年岁,源自草木生生不已的特征。

关于“成”,我们熟悉的“年”字,取象于收获之意。甲文作

,金文作

,用人背负禾谷的形状,表示丰收之义。《说文》:“年,谷熟也。”无论是卜辞中的“受年”“有年”,还是《春秋》中的“大有年”,都表示丰收成熟之义。在中原地区,禾谷一年一熟,“年”因此也有了“年岁”的常用之义。《尔雅·释天》说:“周曰年。”邢疏:“年者,禾熟之名,每岁一熟,故以为岁名。”准确解释了“年”的引申理路。与“年”相仿,还有一个“稔”字。《说文》:“稔,谷孰也。”也因谷物一年一熟,而表年岁之义,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中有“三稔”“五稔”的说法,都是纪年之辞。
时间的积淀,形成了更为悠久的历史。有意思的是,“歷”这个字也源自植物意象。在甲骨文中,已经有了“秝”字,写作

,《说文》说:“秝,稀疏適也。”为禾苗排列均匀分明之象,段玉裁、王念孙皆以此为“调和得当”之义。古文字中还有“厤”字,金文作

,小篆作

,《说文》:“厤,治也。”《段注》说:“厤者,调也。按调和即治之义也。”阐明了“治”与“调和”的统一关系。无论是禾苗的春耕秋收,还是稀疏得当的插秧布局,都体现出内在的秩序特点——在从“禾”的汉字中,程、称、秩、稀、稠,也都与秩序密不可分。时间的规律亦是如此,在“秝”“厤”的基础上,古人造出了“歷”“曆”,添加“止”,表示岁月不断前行;添加“日”,彰显时间与天象的关联,至于历史内在的时间秩序,则始终凝聚在那摇曳低垂的禾麦之中。在中国古人看来,历史不是单一的时间流淌,而是在“逝者如斯”的滚滚东流中,蕴含着内在的规律与循环——无论是“三世”“三统”“文质损益”的历史哲学,抑或是“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”的历史感受,在时光永不停息的进程中,总有冥冥之中的轮转之感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在天人合一的传统中,“生”与“性”同源,时间的生生秩序不仅属于自然,更统摄着人文的世界。在时间的节律中,人类的生命规律、社会实践与文化成长,都具有内在的生生之理。《黄帝内经》中说,“夫四时阴阳者,万物之根本也。所以圣人春夏养阳,秋冬养阴。”四时的属性,统摄着人类的自然成长。在《礼记·月令》等文献中,更详尽规定了人类社会活动的时间标准。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感慨“四时行焉”的天道,提出了“学而时习之”的修身理念。对此,皇侃的《论语义疏》进行了精彩的阐发:
夫学随时气则受业易入。故《王制》云“春夏学诗乐,秋冬学书礼”是也。春夏是阳,阳体轻清;诗乐是声,声亦轻清。轻清时学轻清之业,则为易入也。秋冬是阴,阴体重浊;书礼是事,事亦重浊。重浊时学重浊之业,亦易入也。
皇疏所引《王制》与今本不同,但似乎更得“时习”之义。春天万物萌生,志气亦为之昂扬,故以《诗》言志;夏日草木繁盛,性情亦为之恢宏,故以乐鼓舞;秋天肃杀,精神沉潜,故以《书》明史;冬日寒冷,心灵肃穆,故以礼立节。一个人的人文成长,在四时的统摄下,洋溢出诗意的生命韵律!

在汉字世界中,草木禾谷的萌生与成熟,标志着岁月更迭的生生不息,体现出春夏秋冬的自然节律,更意味着时间背后的憧憬与希望——在磅礴浩瀚的大化流行中不断生成,同时遵循清晰的循环规律,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秩序与历史感受。由草木生生到时间秩序,由时间秩序到人文历史——时间,贯通了天人古今的一切,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精神结构。
(本文发表于《文史知识》2019年第9期)
作者简介

孟琢
孟琢,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文学博士,从事训诂学、《说文》学研究,章黄国学主编。
史瑞雪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2019级博士研究生。

特别鸣谢
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
敦和基金会

章黄国学
有深度的大众国学
有趣味的青春国学
有担当的时代国学
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
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
微信号:zhanghuangguoxue

文章原创|版权所有|转发请注出处
公众号主编:孟琢 谢琰 董京尘
责任编辑:林丹丹
专栏画家:黄亭颖
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|